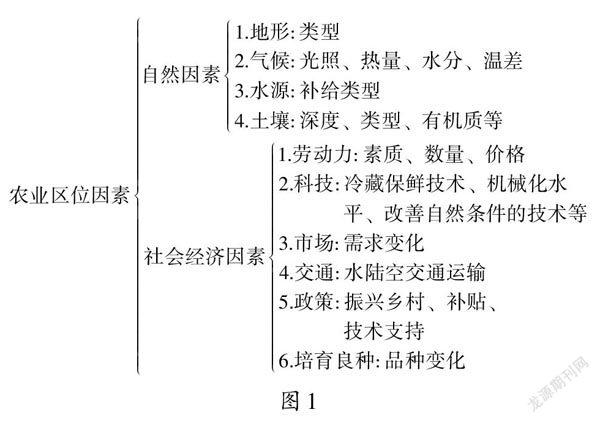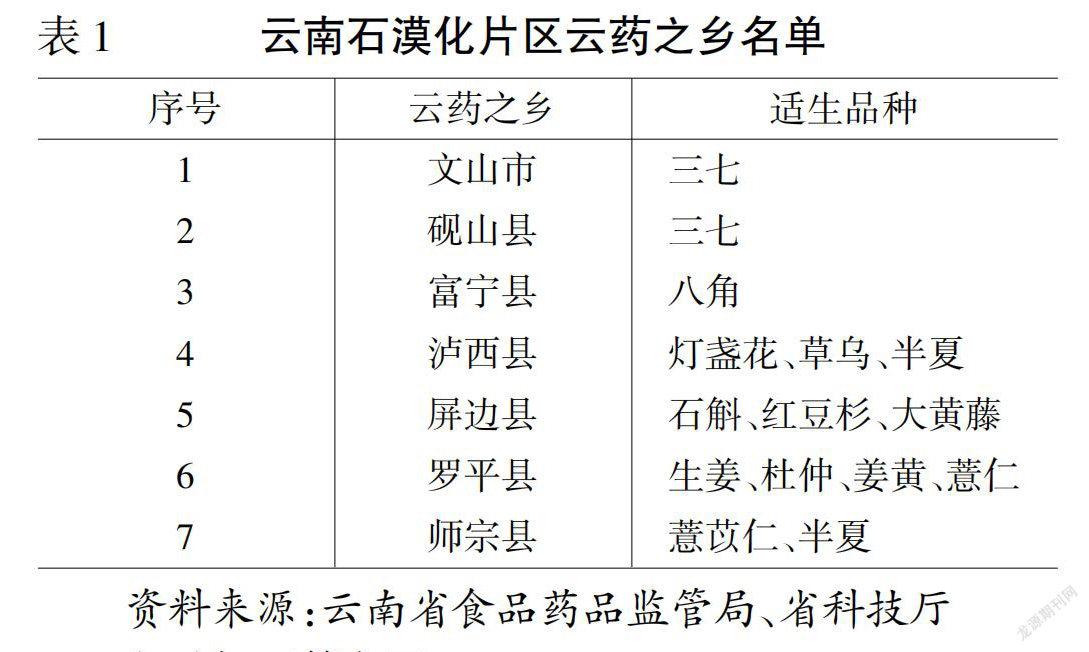【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 李醒民
光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在新冠疫情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之际,日月似乎也运行得格外迅疾。不知不觉间,孙慕天教授(1939—2019)隐化已三年有余。记得先生仙逝之时,我曾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化作一首七言诗:
妙语连珠名师孙,凌云健笔惊四邻。
熟识哈市论苏哲,再晤密山展雄文。
镜泊把酒邀星月,黑河畅怀涤身心。
卌载如梦一闪念,犹记湿地情谊深。
那个时候,就想写篇纪念性的文章,无奈总是联翩浮想刚上心头,却又剪不断理还乱,只好抱憾搁笔。谁知这一拖竟是三年之多。最近,先生的学生拟为其师编辑、出版纪念文集,诚邀我写点文字。作为将近四十年深交的老友,我再也不能让遗憾继续下去了,遂慨然应允,以了数年的夙愿。
先生长我六岁,可算是一代人吧。同代人本来就没有代沟,更谈不上什么隔阂,加之多年多次交往,可谓相见甚欢,晤谈骋怀,情投意合。不管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共赴饭局,我们坐在一起总是直抒己见,口无遮拦,海阔天空地神聊,有时竟聊得不知今夕何夕。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他是后学之良师,也是学界之翘楚。在我的记忆里,先生讲演时口舌生花,妙语连珠,眉飞色舞,激情四射,恰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想,他在给学生上课时肯定也是这样潇洒自如,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他的学生肯定与我灵犀相通,人同此心,心同此评。先生操觚染翰之时,如椽之笔汪洋恣肆,扬葩振藻,璧坐玑驰,蹙金结绣,使拜读者无不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感。不管是研读先生匠心独具的鸿篇巨制,还是翻阅先生随心率性的隽永短文,除了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知识的增进外,也给人以十足的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写到此处,老杜的诗句蓦然跃入脑海:“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藉此形容先生的文辞,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好像这是绝代诗圣千年前专门为先生量身定做的。
在我的心灵深处,认准的只是这样一个单纯的道理:思想和道德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唯有思想和人格才能万古不没。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练,就是有思想的章采和有人格的文德之化境。正如我的“学界与学人”一诗所言:
学苑贵创新,览胜赖天真。
人格须卓立,思想应不群。
好高起平地,骛远秉本心。
章采遗后世,文德留余温。
面对先生,我最佩服的就是其思想和人格。他的思想章采以苏俄科学哲学、新整体论等研究为代表,尤其是前者,在国内学术界首屈一指,在俄国同行中也赢得好评。这已是不刊之论,有他的诸多论著佐证,无须我过多置喙。至于他的道德人格,亲朋、学生、同事已述备矣,也用不着我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在这里,我仅想回顾一下我与先生相识的经过,以及其间发生的一些逸闻趣事。查阅有关资料,首次与先生见面,极可能是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上。此后三十多年,我们几乎年年在学术会议上以文会友,或在私下相聚中切磋琢磨。与先生从倾盖如故到相知恨晚,从彬彬有礼到无所顾忌,还是归因于他亲自发起或参与组织的五次学术会议——这些会议都在其故里黑龙江召开。我之所以选择这五次会议当作陈述的要点,一是这些会议是先生操办的,二是我与先生接触较多,三是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四是正好与上述的七言诗遥相呼应。
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先生在哈尔滨举办“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会后我以双笔名发表了这次会议的报道。先生在大会以“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论及其实践对策”为题做学术报告,由此我了解到先生对苏俄科学技术哲学用功之勤,研究之广,水平之高,造诣之深。我本来对苏俄自然辩证法或科学技术哲学素无研究,好在当时刚刚译完苏联自然辩证法大家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自然科学·物理学》(Б.М.Кедров,Ленин и Научные Ревалюции,Встествазнание,Физика,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1980.),顺便写了篇论文“简论凯德洛夫的科学革命观”提交会议,聊以自慰。先生除了要组织学术交流议程外,还得管理和协调各种会务杂事。会议食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会务组安排得井井有条,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买火车票却是最令人头疼的事——要知道当年交通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便捷。为了保证与会者在哈愉悦、离哈顺利,先生风风火火、瞻前顾后、忙上忙下、马不停蹄,为此赢得“拼命三郎”的美誉。此次会议,使我对先生的人品和学问萌生了钦敬之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会议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叫人忍俊不禁。记得有天下午,大家在太阳岛游览后,纷纷跃入松花江尽情畅游。临近傍晚,刘珺珺老师一行五六人上岸时,不知什么误会所致,衣物不翼而飞。没辙了,他(她)们只好面不改色心不跳,身着泳衣打赤脚,沿着中央大街“招摇过市”,一路引来众多惊异而惶惑的目光。这一逸事在科学哲学界一度传为佳话。
“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密山县召开。我记得很清楚,是在9日半下午由牡丹江转车去密山的。车行半途,只见朗月高照,夜色朦胧,四野静寂得令人惊诧、战栗,只有轮轨单调的咔嗒声。赶赴住地时,已是深夜11时。先生久候多时,热情招呼,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次日的全体会议上,先生发表讲演“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其资料之丰富,分析之透辟,议论之风生,观点之新颖,令人叹为观止。我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覆车之辙,不可不鉴——从凯德洛夫的代表作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僵化思想和简单化做法”。会余外出游览,兴凯湖的浩淼,中苏边界的神秘,虎头关东军地下工事的顽固,乌苏里江的大美,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先生的精心安排和周到运筹,使得与会者交口称颂不虚此行。
2002年8月17日至21日,“第八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和牡丹江镜泊湖召开。先生是会议主持人之一,也是最活跃的参与者。17日上午,我以“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为题做学术报告。18日下午,会议迁移到镜泊湖龙泉疗养院继续举行。幽美的湖光山色激发了专家的灵感,熊熊的篝火晚会燃起了学子的热情,致使学术讨论异常深入,争论辩难格外热烈。我的“镜泊湖龙泉宾馆”一诗记录了其时的奇境和盛况:
如此静谧今难寻,镜泊龙泉涤我心。青山若黛缄私语,白云似簇游无音。旷远蓝天眠湖底,浩淼绿水去畸痕。世外桃源放高论,惊飞野禽隐林深。
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有天晚上饭饱酒酣之后,大家纷纷登上望湖楼楼顶平台,凭栏四顾。是时,皓月当空,繁星灿灿,水波不兴,万籁俱寂。先生及其学生周东启老师触景生情,仰天长啸,齐声朗诵苏轼的《赤壁赋》。兴尽之后,先生与我穿越茂林修竹,沿着石子小径,高一脚低一脚地相伴返回住所——当时社会资源和学校经费都相当有限,与会者一般都是两三人同住一间客房。此刻,“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诗句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晕晕乎乎地洗完澡后,俩人躺在床上漫无边际地胡扯神侃,不知聊了些什么话题,也不知何时沉入梦乡,亦不知东方之既白。
“第十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4日至8日先后在哈尔滨和黑河举行。先生在大会做了“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的报告,我也以“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发言。黑河是我国边陲重镇,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曾有“南有深圳,北有黑河”之说。在参观瑷珲历史陈列馆、乘船游览黑龙江、考察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时,我与先生不时碰面,间谈不已。
2006年8月15日至17日,在被誉为“天然百湖之城、绿色油化之都”的大庆市,举办了“第十一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对于先生和我来说,这次会议堪称温馨之行、幸福之旅。据说,先生前前后后共招收一百多位研究生,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连连长。这次会议,追随先生而来的学生将近一个排,是历次会议中最多的一次。你想想,学生对先生发自内心的尊敬、爱戴、钦仰,先生能不感到温馨?那种众星捧月、绿叶映花的感觉,只有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才有,先生能不感到幸福?先生的学生庞晓光也来参会,在我名下就学刚好一整年。报到那天,我们一到会议住地金三角宾馆,头等大事就是拜访先生。那个欢快的场景,那个投机的言谈,那个活跃的气氛,那个和谐的心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不用说,旷远无垠的东北大平原、壮美兼具优美的湿地风光使人流连忘返,大庆铁人的奋斗和奉献精神、与会者融入自然放飞自我的情怀,令人刻骨铭心。何况还有学问的切磋,思想的交流——先生在大会做了“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和比较科学哲学”的讲演,我也就“科学与人的价值”发表了自己的一得之功、一孔之见。
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博览中外名著。学成之后,又特别努力勤奋,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先生成为德高望重的名师、铄古切今的学者,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先生功成名就,是扎扎实实学出来的,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是实至而名归;
而不像当今某些学界中人,是靠大吹大擂吹出来的,大轰大嗡轰出来的,大捧大拍捧出来的。先生一生没有白活,没有枉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先生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含笑于九泉之下,远离乱耳之丝竹、劳形之案牍,高枕安寝,永久地歇息了。
作为先生的同道和良友,我还是为先生小有惋惜。一是先生在八十年代为何不来北京求职?要知道,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0年代正是先生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之时,而北京的众多学术机构和大学个个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家家求贤若渴、虚席以待。也许是先生留恋养育自己的肥美黑土地,也许是先生不想远离亲朋浪迹天涯,也许是先生不愿失去已有的学坛和人脉?假如先生当年能够立足、扎根于北京学界,肯定会生产更丰硕的学术成果,产生更深远的学术影响,毕竟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是世界的科学和人文荟萃之地。二是在眼下的中国,先生享年虽说不上短暂,但绝对不是高寿——我觉得高寿应该年逾九旬。先生当然是老人了,可是思想和心灵依然年轻,有说不完的话题,写不尽的文字。倘若先生能够在人世多待一二十年,无疑能够畅抒雅怀,挥洒珠玑,笔走龙蛇、频现佳作,给人间留下更多精美的精神食粮——这也是先生烈士暮年的雄心壮志。先生赍志而殁,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在此,我要为先生坦露天妒英才之怨,直抒壮心未央之憾。不知先生在彼岸世界以为然否?
不过,话说回来,先生有幸在世创造了自我的思想,丰富了人类的文化。仅此一点,先生就没有虚度人生,就没有枉做一个读书人——须知唯有思想才是伟大的,唯有文化才是恒久的。站在历史的长河来看,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在于独特的创造和贡献,而不在于平庸的过活和长寿。有所创造和贡献,即使未足终天年,也不负来人世一趟。不创造,不贡献,光知道索取和享受,就是度百岁乃去,也是苟且偷安——除了消耗或浪费地球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外,又有何益?我的近作“为先生逝世三周年而作”,表露的正是这个意思。在此不揣谫陋,我愿把它奉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愿与先生的学生和亲朋分享我的感悟和情意:
生死虽常态,彭觞仍不齐。
留取邕文在,何须寿期颐!
[1]李醒民、黄亚萍:记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1983),第6期,第72-75页。
[2]关钟、扈丁: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1984),第6期,第75-76页。
[3]孙玉忠: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讨论会在黑龙江召开,《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1988),第1期,第72-73页。
[4]会议秘书组:第八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纪要,《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8卷(2002),第10期,第79-80页。
[5]吴永忠、李杰:第十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纪要,《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1卷(2005),第5期,第109-110页。
[6]庞晓光:第十一次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发展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8卷(2006),第6期,第105页。
[7]扈丁:追寻生命的永恒——傅伟勋教授与《世界哲学家丛书》,《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2月18日,第10版。李醒民:最伟大的是思想,最恒久的是文化——《批判学派与民国时期的科学论》作者后记,《民主与科学》,2022年,第2期,第74-77页。
猜你喜欢 哲学学术会议 《八七会议》党员文摘(2022年15期)2022-08-04欧洲理事会会议环球时报(2022-04-07)2022-04-07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考试与评价·高一版(2020年3期)2020-11-02主席团会议时代青年·视点(2018年1期)2018-03-26酷巴熊的生活哲学高中生·职教与就业(2013年1期)2013-07-24目击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0期)2013-05-14英文目录及摘要社会科学(2009年9期)2009-10-22晾衣哲学视野(2009年20期)2009-04-09幽默哲学视野(2009年6期)2009-03-10董进霞 治的是学术 过的是生活中国体育(2004年3期)2004-11-11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410/582333.html